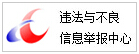2007年七月,父母来南方探望我,我趁工作闲暇之际带他们游历了各个南方城市,看的出父亲漫不经心南方的城与山水,心中不免有所失落。近年来,已过古稀之年的父亲身体不免出现些状况,每当这时老人总是念叨,他有生之年还有一个愿望,就是能再次回到他度过二十多年军中之旅的第二故乡,也是我儿时初有记忆的地方—厦门;望着父亲日渐渴望的目光,我决定遂了他的心愿,专程请假陪伴二老回“家”看看,听他说说那过去的故事。于是我与二老在一个骄阳似火的日子来了厦门;虽漫步在美丽而浪漫的厦门岛,却屡屡与父亲艰难而坚韧的青春不期相遇,使我邂逅了父亲平凡人生中最具魅力一段历程,我想用平凡的文字承载他的青春,以呼应他当年的最朴实无华、无怨无悔的真诚岁月。
之一、鼓浪屿之歌
鼓浪屿四周海茫茫,
海水鼓起波浪,
。。。
只见云海苍苍
我渴望,我渴望,快快见到你,
。。。
萦绕我心中已久早已熟悉的旋律和父亲的愿望,伴着我们乘坐的轮船驶向碧海环抱中的鼓浪屿,我看见老父亲嵌满岁月风霜的脸上露出了一份庄严;十九岁入伍,人生的第一站就是在鼓浪屿,这里意味着他人生的起点,一呆就是十年没回老家。
踏岛第一景点,我们被一个导游游说去了海洋世界;出来后,急于去“老地方”的父亲坚决推辞了导游的一番“美”意,坚持按自己的记忆游览,我本就有这次全程随他老人家意愿的打算,也就挽着妈妈,随父亲走进了鼓浪屿的小巷。岛内街道短小,纵横交错,清洁幽静,空气新鲜,树木苍翠,繁花似锦。
无暇顾及岛上的美景,我们来到了鼓浪屿好八连的营地。父亲指着营地大门对面的小楼说这是他入岛的第一宿营地,小楼大门还开着,我们没有进去,父亲伫立门口,抬头总是望着二楼的窗户;原来当年父亲经常下了岗哨,乘着夜色下海洗澡,回来把换洗完的衣服晾晒在二楼的窗户上;海风袭袭,衣服常被吹落在我们脚下的位置,那时没有多余的军服,他们那些兵很珍惜那些衣服,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奔下楼来拾起衣物,父亲笑了笑弯腰示意。我举起相机,与父亲的青春—我是一个兵相遇。
小巷的路缓缓向上延伸,象是父亲走过的军旅之路,父亲讲述解放初期,岛上这一带美蒋特务出没频繁,父亲所在的部队驻扎在此,备战巡逻任务很重,父亲凭着一腔对祖国热爱的青春热情,不怕苦不怕危险,任何任务来时总冲在前面。由于表现突出,1955年,也就是父亲入伍四年之后,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第一次军衔制时,父亲被授予军官军衔,虽是军衔中最低的军衔,对于从小是遗腹子与母亲相依为命长大的父亲,是终生难忘的;授衔仪式是在厦门大学大礼堂外面的操场上举行的,父亲成为当年共和国最年轻的军官之一,每当说到这父亲身板挺直,我犹如又见到了家中影集中那幅身着军装透着英气的父亲。
随后来到了几处不知名的民居小楼,没有什么游客,树木郁郁葱葱,很是清幽,都是父亲生活成长居住过的地方。每到一处父亲总是一个人冲到楼很近的地方,驻足很久;我自然很配合的给父亲留下难忘的身影,且选择父亲站在有树的地方,希望已年老的父亲有树的映衬显出更苍劲的一面。
出了巷子,我们去了菽庄花园。景观介绍菽庄依海建园,海藏园中,傍山为洞,垒石补山,与远处山光水色互为衬托,浑为一体。顺着海边游览,父亲告诉段我从没听过的往事,母亲来过这海滩,原来当年新婚的母亲曾来探望过父亲,看过母亲年轻的相片,很是清秀文静;我想象着当时的情景,园内看海,波浪拍岸,依栏远眺,极尽山海之致,父亲的青春也不乏浪漫的元素。家中长女的我,从没有象今天这样自然的搀着父亲挽着母亲散步,幸福象花一样在我心中滋长。
每日凌晨,朝阳从厦门五老峰后升起,日光岩是厦门最先淋浴在阳光中的地方,是游人们来厦门的必登之处。从老相片中得知,不足周岁母亲便带着我从家乡随军来到了厦门,母亲和父亲曾抱着那时的我登上了日光岩的顶峰,从此我童年记忆的篇章也始于厦门的日子。登日光岩,父亲也没带我们直奔主峰,我们先是来到了郑成功纪念馆,这里曾是父亲团部所在地,父亲曾端着枪在这站过岗,纪念馆门前自然又多了一幅父亲与青春相叠的剪影。绕过纪念馆的“皇”竹林,我们便向上攀登,经“一片瓦”向上,要路过一个石砌的长方型石门,父亲停下了,就是这,我这第一次站岗的地方,防止有不法分子偷入顶峰,与现今多么不同的内容,不经意间遇到父亲最稚气的青春,我不禁惊叹于父亲的记忆了。立于石门下的台阶拍照,仰视着父亲,正是夕阳逆光背影的时候,父亲古铜色的脸格外严谨,无论如何我勾画不出当父亲年稚嫩的身影。
过“古避署洞”、“龙头山遗址”、“水操台”,我们终于登上了顶峰“百米高台” 。故地重游,天风簌簌,吹走了我幼时的脚印,我们倾听海涛,看八方美景;脚下的鼓浪屿,各种风格的建筑错落有致,象钢琴岛上弹奏出来音符,凝固成一曲最浪漫的旋律;眺望远处,水天一色,越过海峡,就是宝岛台湾。我寻着父亲,正凝视远处,肯定在想念他当年的战友们和守候在这的日日夜夜。快乐的游人穿梭如云,何曾想在他们身边还有一位四十多年前与百米高台曾经风雨的老人;按捺不住的心情,按捺不住的镜头,我留下了思索中的父亲。
父亲的青春没有动人的旋律,可青春的背景是动人的鼓浪屿,注定我会为父亲的青春心动。
之二.面向大海
第二天,父亲提意行程自由,我们便包了辆的士环岛行驶,清晨一路领略阳光、大海、沙滩、草地、绿树、鲜花和红色人行道等天然与人工的美景,可谓心旷神怡。我们来到了溪头黄厝,父亲当年曾在这随部队驻守这段海岸线,当年这里很荒凉,人烟稀少,如今厦门的一大著名景点—台湾民俗村座落于此。
也许是位置偏僻、又是旅游淡季,民俗村内游人甚少。入园后,我们观赏了民俗村的蝴蝶生态园、台湾山地歌舞、十二生肖园、日月潭等,还游览了景洲乐园的欧式园林景观。到了金山脚下,已是午时,阳光灼热,我和母亲坐在一个亭子的石凳上,满面倦意,再好的风景也诱惑不了我们前行。老父亲却精神抖擞,想到金山顶上的松石亭,眺望至今还属台湾管辖的几个海上岛屿,执意登高。
将孝心进行到底,只好搀母亲随父亲一路盘山而上,无心看奇石金松,观佛手莲花,只想快点登上最高点;过了一个时辰后,只觉一阵清风拂面而来,还有几十步台阶处的松石亭已跃入眼帘,父亲大笑道,再难的路我也走过,还怕了他不成,径直大步登了上去;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,我和母亲终于随后登上松石亭。亭阁里不时悠悠拂过清凉的山风,带走了天气的酷热和我们的倦怠,父亲与母亲凭栏面向大海悠闲而坐,我想起了老人与海的故事;环顾四周的景色,金山巍峨壮丽、奇石蕴玉;郁郁葱葱、婀娜多姿的松树,远望黛绿秀美,真似人间仙境;纵伸大海,就是大小金门、大担、二担等几个岛屿,其中小金门岛,因当年台湾局势紧张,是国防部队最重要的防卫对象。父亲还说起了一段关于金门岛的往事,解放初期部队曾攻打过小金门,当时条件简陋,只能乘普通的渔船攻岛,加上船只数量也少,部队只派出一个团的兵力,国民党等候我们部队上岸后,偷袭放火烧了渔船,断了部队的后路,部队没有船只援助,一个团的兵力全部折损,杳无音信,从此部队只采用以守为攻的战略。
父亲告诉我当年他们白天就在金山脚下修筑工事,战壕一挖起码在两米深以上,沿海岸线到处设防,父亲他们完全是靠着锹、锄等简易工具和双手挖掘,加之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,精神高度绷持,那种苦是无法形容的,但战士们没有叫过苦,纯奉献精神在那个年代体现的淋漓尽致。为了防止“海鬼”国民党特种兵上岸,清晨和夜间还要在战壕或海滩的沙堆里站岗;风雨天海面漆黑,看不见任何情况,他们就趴在沙滩上,卸下枪上的通条插入沙地,耳朵贴近通条,来监听听周围的动静,沙子打在脸上生疼,他们也不敢有一丝疏忽大意。
父亲还告诉我个趣事,胡里炮台对面大担岛上有座庙,被国民党把守着,天天清晨传来的钟声格外洪亮,缭绕在我们前沿的上空,象是对着我们的部队示威;1952年年底,父亲所在的陆战队在胡里炮台向着大担岛发射了几枚炮弹,从此大担岛上再也没有传来钟声,扰我军心。
在溪头海边一带,父亲十几年的岁月基本上是在战壕和海滩上度过的,父亲的青春不知不觉时时面向大海,从寂寞庄严中走过。当年他们修筑的工事炮台,已成为了历史的见证;金门岛如今民间已通航,两岸向和平统一已迈出了新的一步,但台湾的局势不容乐观,父亲感慨四十几年后的今天,他们的下一代还在为实现他们当年的和平统一愿望努力着。
在松石亭,我把镜头伸向远方转了一圈,寻找着当年父亲和他的战友挥毫保卫和建设祖国篇章的背影,时空还我一个宁静的大海,我只能在父亲的述说中感受他艰苦奋斗不失壮志的青春。
下山后,我们应父亲的“邀请“,沿海边寻觅当年他巡逻站岗的足迹,黄厝、白石炮台、塔头炮台、胡里炮台、厦门大学后门及一些无名沙滩的海边,每到一处对着镜头父亲总是神情庄重的面向大海、脱帽、双手笔直垂下、脚踩沙地留下背影,那是他对当年面向大海站岗姿势的重现;开始我和母亲对父亲的举动感到十分搞笑,大海衬托下的背影渐渐地的在我的镜头前变的高大起了,慢慢地我理解了他的这份虔诚—一份对自己追求无悔的纪念,他的信念来自他对他信仰事业的忠诚,哪怕他已老了,他的事业不需要他了,他需要是坚守他心灵的一块阵地。我在他的身前身后忙碌着,不厌其烦的替他拍下只有大海映衬的背影,相信父亲的眼前是个极其美妙庄严的世界,大海赋予他最宽阔的胸怀。此时的父亲在我眼中简直就是个坚毅不可摧的可爱老头,真想搀他的手,扶他上马,策马扬鞭,再驰人生又一程。
父亲的青春就这么尽收眼底,亲密接触父亲的青春,我汲取的是那份真诚,那份我们早已久远了信念;我重新认识了一个全新的父亲,没有轰轰烈烈的一番事业,却曾想在这座海上花园城市,留下一幅幅实实在在的青春印迹,持枪、背影、战壕、坑道、炮台甚至铁锹、木棍、汗水、血水已演绎成城市历史特定的一幕,厦门终究是我心中最美最使我回味的城市。
夜幕来临,父亲和母亲在沙滩上漫步,夕阳的余辉挥洒他们的身上,对面鼓浪屿岛上的音乐又开始飞动起来,青春不在,青春又似永在,在我的笔下延续,我在心底默默祝福他们和那些似不为而胜为之的人们。
结束语:父亲回来后,在外孙女的帮助下写了篇游记,名为《我第二次到厦门的回忆和后感》,无奈他只有早年在军校进修的文字水平功底,千真万确是篇的“老样板”类型的文章,自己不甚满意,倒着实把外孙女笑的前仰后合。刚才来电话说把当年的事件整理成了纪实性的文字,下次带来给我,可我想那已不太重要了,重要的是我领会了他最重要的部分,所以有意送父亲这篇基本纪实的朴素文字,想必父亲能看懂,我心足矣!
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五日


 皖公网安备34180202000439号
皖公网安备34180202000439号